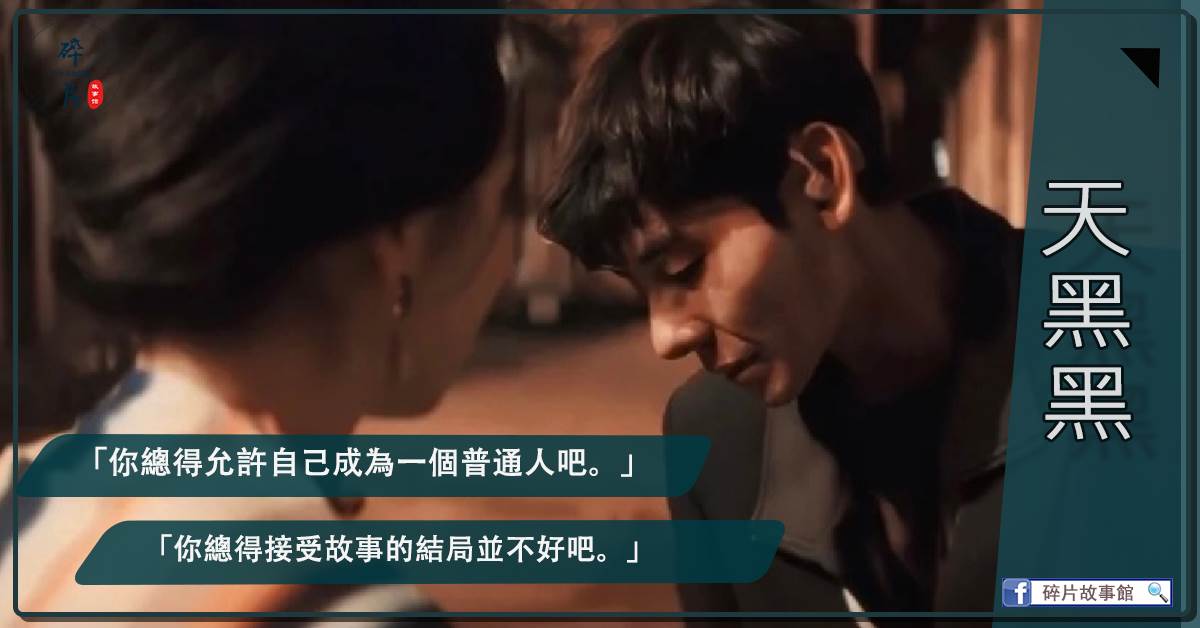《天黑黑》第10章
容遠這該死的,從不撒謊的毛病改一改好不好。
子彈啊。
穿透容遠的身子。
我虎口麻,耳朵疼,我張了張嘴,我發現自己怎麼也發不出聲音。
容遠跪在地上,大片大片的血跡從他腹部蔓延開。
我從沒見過這麼多血。
是從容遠身上流下來的。
我的容遠。
我親手開的槍。
他捂著肚子。
跌跌撞撞地站起來。
他抬起眼睛看我,像是扎染了玫瑰的黑曜石。
血紅而耀眼,狠狠地刺在我心上。
他朝我笑了。
笑了。
他說。
「做得好棒,小溪。」
「你是個能做出自己選擇的人了。」
「……」
我手抖了,我握不住槍了,槍跌落在地上,轉了好幾個圈。
我想這是一場噩夢,就讓我醒來吧。
我想別嚇我了,我和容遠是不是還睡在旅館的床上。
可是,他的身體好真實。
他怎麼不熱了呢。
我一點都沒辦法朝他取暖了。
是他流了太多血的緣故嗎。
他的身體就靠在我身體上。
我們還是像兩只取暖的動物。
只是一只動物現在傷得好嚴重。
被另一只打傷的。
我覺得人聲好吵,我覺得圍觀的人很煩。
如果沒有這些人,我一定會吻他的。
他撿起了地上的槍。
然后將槍管抵在了我額頭上。
我聽見他提高了嗓音,是對外圍的警察說的,喊完這些話,他用盡了最后的力氣。
他說。
「把我昨天在 214 號店訂的東西送過來,可以嗎?」
「不然我會崩了這個女孩。」
那柄槍的槍管口磨了磨我的額角,有點燙。
為了我的安全,警察很快就照做了。
不多一會,人群中散開一條道。
一個警察捧了一盒好大的東西走過來。
遠遠地遞到我們這里,然后慢慢退開。
容遠咬開了那個盒子。
給我看。
……那是一捧嬌艷欲滴的玫瑰。
他的槍還抵在我額頭上。
他的話語全埋在我的頸窩,
輕輕的,又柔和又溫柔。
「520 禮物。」
「喜不喜歡?」
好煩啊。
這是個激情解救人質的現場。
我們卻在談情說愛。
可我真的沒有辦法,我們沒有時間好好思索。
于是我們只能掏取畸形的片隙。
我想把他身上殘留的溫度剝開來,然后再拼湊成完整的一個他。
我想問他,以后你能不能不要去我夢里。
我承擔不起對你的想念。
「小溪,我……」
他揚了揚頭。
開口說。
后面的。
我不知道了。
人生總是這樣,你來不及下車,他就把你趕下車了。
你來不及告別,他就說,話你一輩子都別想說出來。
一枚子彈嵌進了他的心臟。
很準,立即擊斃。
我聽見他們說,「立即解救人質!」
我想,或許是容遠頂著那把手槍頂在我額頭太久,他們覺得容遠要殺了我。
其實這一切,
都不太重要。
如果讓我寫個故事,我就寫,在故事的最后,王子睡在了公主的懷里。
那捧玫瑰花成了飄飄揚揚的玫瑰花瓣。
我把他們撿起來。
我好像撿不完。
我很惱火。
于是我哭了。
容遠在我懷里沒有溫度了。
我再也沒有取暖的人了。
以前我覺得是取暖重要。
現在才發現是他這個人重要。
真的。
現在。
才發現。
30
人生啊。
人生是曠野中的麥穗,是無邊潮汐里的灰煙。
我走過了一場雨地,有人闖進我的傘下。
他俯過身朝我笑。
后來他揉揉我的腦袋,又走了。
我允許我對他的想念。
但是。
每天只能想念一點。
-完-
白框太子凉
作者評論:我知道大多數人會在程序正義和結果正義裏選擇結果正義。可我依舊還是選擇寫下這個結局。容遠做錯了嗎?在程序正義裏他錯的非常離譜,容遠做的對嗎?他也許貫徹了他自己的結果正義。
可人性其實是非常復雜的,小說裏描寫不出十分之一,單拿那個面館的老板來說,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文中的一個細節,小女孩在容遠揮下刀時是護住爸爸的。如果面館的老板死了,那麽他失去的是他這條命嗎?他一整個家庭都會崩潰,男孩女孩失去了爸爸,頂梁柱散了,小女孩會覺得是自己害死了爸爸,在他童年時有個人為了貫徹正義殺死了他的至親,她會感謝容遠還是會恨容遠?
女主開槍打傷了容遠(這裏我想說一下,容遠不是女主殺死的,子彈打進腹部人還能蹦跶好一陣呢,來救護車是能救活的)因為她只有開槍才能阻止他,容遠殺了那個面館的老板不會有任何改變,只是又為了他的罪名加上一條,殺人犯,殺人犯還是殺人犯。那麽面臨他的是什麽?死刑,死刑,還是死刑。人這種東西真的很復雜,情緒化的感官也是,所以我們需要法律的條條框框束縛住我們,羅翔老師說過,如若自由不加以限製一定會造成強者對弱者的剝削。所以我覺得給惡人一刀的一直都不該是容遠,而是《刑法》,是法律,這就是女主開槍的理由。
當然,你覺得愛情至上,為了愛人女主幫男主打死了面館老板也可以,說不定這就是平行世界裏發生的故事呢,最後男女主雙雙坐牢。
其實我不想討論三觀的問題,因為大多時候的三觀正確不過是:「我的三觀和你的三觀相同,所以你覺得我的三觀正確了。」我就想單純寫個言情虐文,單純寫個小說,嗯,兩個人相愛,可惜他們又不得不分開。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