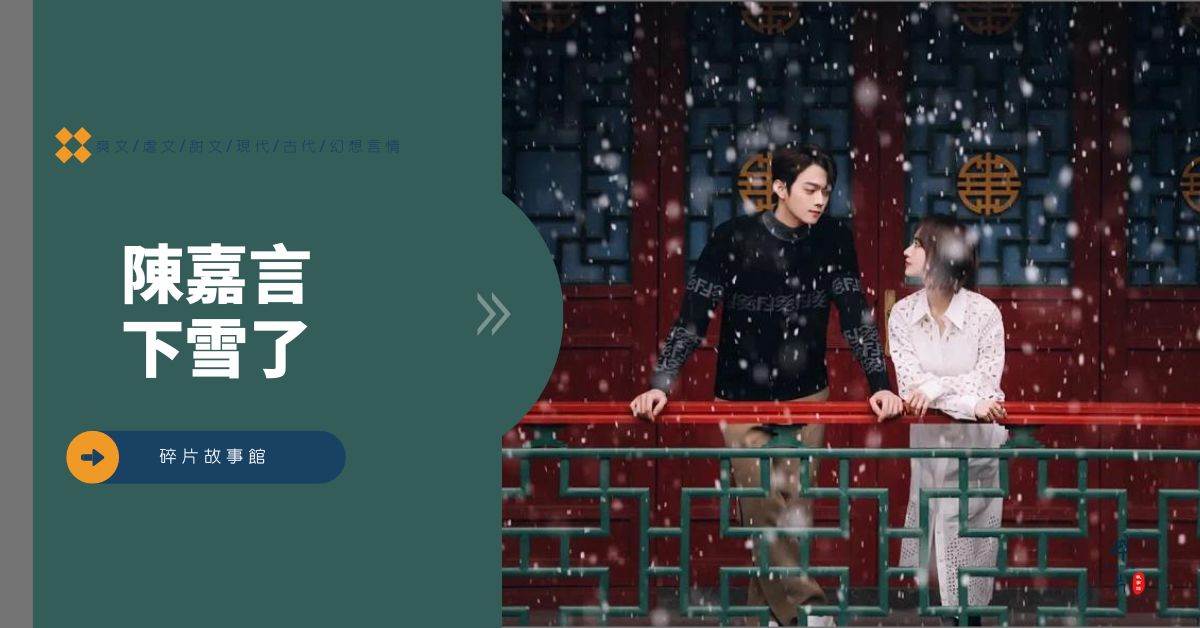《陳嘉言,下雪了》第3章
」
我看著她轉身出去,身影活潑靈動,讓助理將那個盒子拿出去丟掉。
他在我身邊很久,最是知道我對陳嘉言的在意。
「大小姐,要丟掉嗎?」
「嗯,丟了吧。」
這不是陳嘉言送的禮物。
這也不是陳嘉言能做出來的事。
他好不容易擺脫我,只會和我,一輩子老死不相往來。
9
我洗完澡正在護膚的時候,宋慕原醉醺醺地進來了。
「寶恩。」他走到我身后,俯身親我側臉。
我抬手,將他隔開。
「談談吧。」
宋慕原扯了領帶,瞇了桃花眼看我:「談什麼?寶恩,今晚是我們的洞房花燭夜……」
我面無表情地看著鏡中的自己,打開眼霜,認真地按摩著眼尾。
「你在希爾頓酒店總統套房常年養著你的初戀女友……」
「你知道?」宋慕原的呼吸驟然急促。
「對,我知道。」
「那為什麼你會嫁給我……」
「因為我知道你心有所屬。」
我轉過身,平靜看著他:「不會把心思用在我身上,這也正是我想要的。」
「你想怎樣?」
「不怎樣,我們這樣的人,演一對恩愛夫妻,應該很擅長的吧。」
「你不會為難她?」
我搖頭:「我對你的事,沒興趣,只一點,別拿到明面上來,打我和梁家的臉。」
宋慕原看著我的神情很有些復雜。
好一會兒,他才輕嘆一聲:「寶恩,其實我是想要好好做你的丈夫的……」
「做我需要的那種丈夫,才是最好的丈夫。」
宋慕原沉默片刻,方才自嘲一笑:「好。」
10
我結婚后的第十天。
原本就身體極度虛弱的母親,忽然昏迷不醒。
送去醫院搶救的第三天,她陷入彌留。
我攥著她的手,聽著她含混不清呢喃哥哥嫂子的名字。
一遍一遍,不愿停下。
直到最后,她咽下最后一口氣落下最后一行淚,卻至死不肯閉上眼。
病房外站滿了人,面上的悲傷都那麼虛假。
我知道他們盼著母親死,盼著我也早點死。
盼著長房的人,都死絕呢。
我跪在母親的床前,那一瞬才知道,原來人傷心到了極致,是哭不出來的。
母親下葬后的那個深夜。
我將自己關在房間里,不吃不喝。
極度的痛,心臟仿佛都被寸寸撕裂。
卻仍是哭不出。
左手手背已被自己無意識抓得鮮血淋漓。
淚腺漲得生疼,可一滴淚都落不下來。
有那麼一刻,望著黑漆漆窗子,心里竟有個聲音在瘋狂叫囂。
「跳下去吧梁寶恩,跳下去,就一了百了,所有痛苦都會到此為止。」
「你和你最親最愛的人,就能永遠在一起了。」
手機在地板上不停的震動,將我瀕臨瘋魔的思緒緩慢撕扯拉回。
我忽然像是瘋子一樣抓起手機,就要狠狠摔在地上。
可屏幕上「陳嘉言」三個字,卻讓我忽然安靜了下來。
11
「寶恩。」
陳嘉言的聲音傳到我耳邊時。
我竟覺恍若隔世。
這輩子我只有兩個執念。
一求至親都能在我身邊。
二就是陳嘉言。
可我最親最愛的人,一個一個都離開了我。
我愛的陳嘉言,他自始至終,不曾將我放在心上過。
我木然地望著漆黑的房間。
手背上傷口中的鮮血,一滴一滴落在地板上。
「聽說香港今年冬天會下一場雪。」
陳嘉言的聲音很低很輕,沙啞地顫栗著。
我的眼皮微微動了動。
「寶恩,香港下雪那一天,我回來找你好不好?」
「找我?」
「對,你從前不是說,好想香港也能下雪嗎?」
我的嘴角微微勾了勾,眼淚卻撲簌簌地掉了下來。
「不是永遠都不回香港了嗎?」
陳嘉言沒有回答,我卻好似聽到了一聲很低很低的呻吟。
「陳嘉言?」
「寶恩,說好了,香港下雪那天,我們再見面。」
他說完,不等我再開口,就掛斷了電話。
我再打過去時,就再無人接聽了。
同一時刻的機場。
十幾輛豪車圍出的一片空地上。
陳嘉言趴在地上,鮮血從他的褲管里不停涌出。
他的左腿小腿骨大約已經碎裂折斷,呈現出一種扭曲的姿態。
劇痛讓他時而暈厥,時而卻又痛得清醒過來。
「梁先生說過的,你若敢回香港,就打斷你一條腿。」
「陳先生,好自為之吧。」
「把人送醫院,梁先生交代了,好好給他醫治,到底年紀輕輕的,還是個大才子,前途無量,可不能殘廢了,咱們梁先生信佛,心善著呢。」
陳嘉言被抬上車。
鮮血淋漓一路,他染著血的手,努力想要去夠到地上的那只手機。
可響著的手機,卻被人一腳踢開,頃刻間碎裂了。
他的手從擔架上重重地垂落。
那張清俊卻又蒼白的臉上,烏黑的眉,緊閉的眼。
像是最上等的墨,畫在宣紙上的幾筆傷心。
深長的眼尾處,洇出一道一道的濕痕。
淚痕卻又沒入他的鬢發,消失無蹤。
12
母親下葬后百日。
我去墓地祭拜。
穿黑衣黑裙,胸前簪著白花,清瘦孑然,素面朝天。
但不管怎樣,自那夜后,我仿佛重獲新生。
卻也仿似變了一個人。
身后站著數十名黑衣持傘的保鏢,皆靜默安立。
我放下花束,轉過身來。
保鏢忙舉傘為我遮住綿綿細雨:「大小姐,方才墓園那邊有人想要進來,說想見您。
」
「是誰?」
「她說叫宋淼淼,您結婚時她來參加過您的婚禮的。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