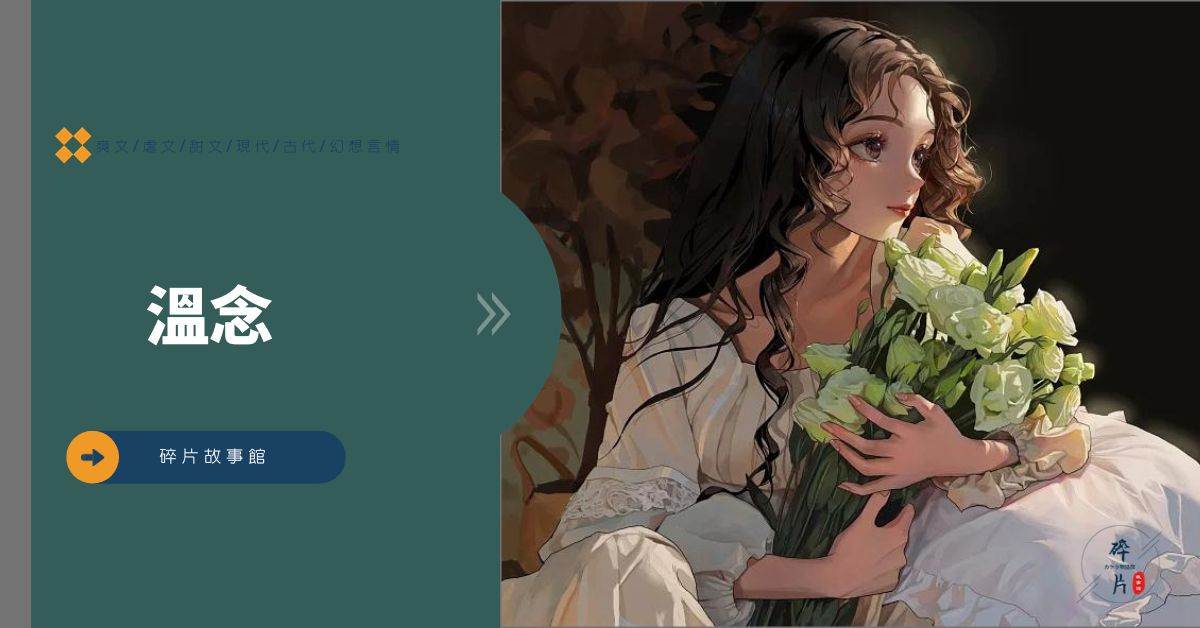《溫念》第4章
轉瓶吧,下一個是誰?」
游戲繼續,這次瓶子轉到陸宣怡的位置。
轉瓶的人提問:「挑在座的一位,說一說他做過讓你印象最深的事。」
倒是個正常不過的問題。
陸宣怡含笑看向身側的宋岑,眼底冒著粉紅泡泡。
「我選宋岑哥。」
她不知想到什麼,邊回憶邊眷戀地說:
「七年前,我還未出國,那時我們在鬧別扭,宋岑哥高燒 39 度與人賽車,只為贏得第一拿獎牌哄我。只可惜,他駕駛失誤,不小心翻車傷了腿......」
大家聽了,嘶氣聲一片。
而我聽后,手中的酒杯滾落在地,心下掀起滔天駭浪,不可置信看向她。
宋岑因我方才的話還在失神,等他反應過來時臉色巨變,攥緊陸宣怡的小臂將她帶離座位:「抱歉各位,她喝多了。」
「放開她,宋岑。」我從椅子上站起,「讓她把話說清楚再走。」
陸宣怡大力掙脫宋岑的手,指著我:
「你算什麼?你不過是我的一個替身!宋岑哥愿意為我飆車,為了我不顧一切反抗家里。宋家當年為了分開我和他,攀上江家,才會編造謊言,將他受傷說成是為你擋車!你不過就是命好,所以大家都圍著你轉......」
「啪!」
「夠了!」
陸宣怡捂著臉,不可置信看向眼前的人,喃喃道:「你竟然為了她打我?!」
「陸宣怡!」宋岑面色冷硬,決絕地說:「你要鬧到什麼時候?我早就和你說清楚,我們已經結束了!」
陸宣怡哽咽:「可是你那天還吻了我,你捫心自問,真的就對我一點感情都沒有了嗎?」
說著,她委屈地哭了起來。
宋岑陰沉著臉:「若不是你威脅我,要將這件事說出來,我根本不會碰你。
」
我冷眼看著他們,胃里一陣惡心,好,真是好。
我拿過椅背上的包,一分一秒都不想再看見這兩個人。
宋岑眼底閃過一抹驚慌,上前攔住我,臉上悔恨與愧疚交加。
「念一,這件事我可以解釋,我也是有苦衷的。你不能就這樣對我判死刑!」
見我不為所動,他拿過桌上的空酒瓶對著墻壁一砸:「念一,為了你,這條腿不要又如何!」
說著,竟拾起地上的碎片往膝蓋扎,很快,淺色西褲上暈開一片鮮紅的血跡。
大家被他的舉動嚇壞了,想上前阻攔,卻被他用碎片揮開:「別過來!」
我一點點掰開他揪住我衣擺的手,對他手上的血視而不見,語氣毫無波瀾:
「你自以為的深情是為了感動誰?你踐踏完我的心,卻妄想它憐惜你?」
「你就算是死在我面前,我也不會流一滴淚。」我搖搖頭,指著心臟,「你可以試試,是你的命硬,還是我的心硬。」
說完,我不再留戀,大步離開。
8
七年前,我在醫院醒來,失憶忘記閔村發生過的一切。
我永遠都忘不了,剛醒來時心臟那種瀕死的窒息感,我不知道要去哪里,赤腳沖出病房,不顧一切地往外跑,直到腳底被尖銳的石頭扎傷,流了一地血。
我只知道,我要去找一個人,卻不知道要找的是誰。
我迷茫地看著馬路上的車流,第一次生出無力感,蹲在地上嚎啕大哭。
后來,大家都告訴我,是一個叫宋岑的男生救了我,為此他右腿粉碎性骨折,全身多處挫傷。
初見時他的脾氣很不好,我姑且歸咎為是因為救我受傷,傷重疼痛難捱,偶爾作一點也能忍受。
我每日雷打不動給宋岑送飯。
門推開那瞬,迎面飛來一本半指厚的字典,我往旁邊躲,字典磕在地板,發出悶響。
「誰叫你來的?」床上的人右腿打了石膏,高高架起,質問聲依舊中氣十足。
我把東西撿起來擺好,安慰他:「醫生說你只是骨折,不是截肢了。好好休養會好的。」
「呵。」他似乎被我氣笑:「你可真會安慰人。」
我動了動鼻子,嗅到空氣中刺鼻的味道,一把掀開宋岑的被子,果然,里面藏著麻辣小龍蝦,辣子雞,烤串。
「喂,你是狗鼻子嗎?」他趴下身子,長臂攬過牢牢護住那些「贓物」。
要從一個病患手里搶東西可謂輕而易舉,我奪過他懷里的東西,全部沒收。
「你現在還需戒口,不能吃這些。」我倒出保溫壺的雞粥,放他面前的小桌子上。
我背過身,準備喝口水,背上一股黏膩的熱意,伴隨著劇烈的灼痛感。
宋岑手握空碗,臉上是掩蓋不住的惡意:「現在吃不了了。」
說著,嗤笑將碗扔到我腳邊,閉眼往床上一躺。
「退下吧,我累了。」
我擰開蓋子,把剩下的粥從他頭頂倒落。
床上的人避無可避哀嚎一聲,猛地將我推開:「你是不是有病?」
后腰撞上柜角,很疼,但很解氣。
我早就受不了他了,要不是他救過我,我早就將他的臭臉摁馬桶里了。
那之后,宋岑不敢再無事生非,連帶著對我的態度都好了不少。
相處下來發現他人不壞,就是被家里寵壞了。
后來,總會有一個拄著拐杖的背影,跑遍大街小巷,提回我愛吃的零嘴,只為討我歡心。
他生日那日,趁關燈吹蠟燭的空隙,他悄悄握緊我的手:「我的救命之恩,你好像沒還。
」
我回望他,他眸中光明明滅滅,倒影出我的影子。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