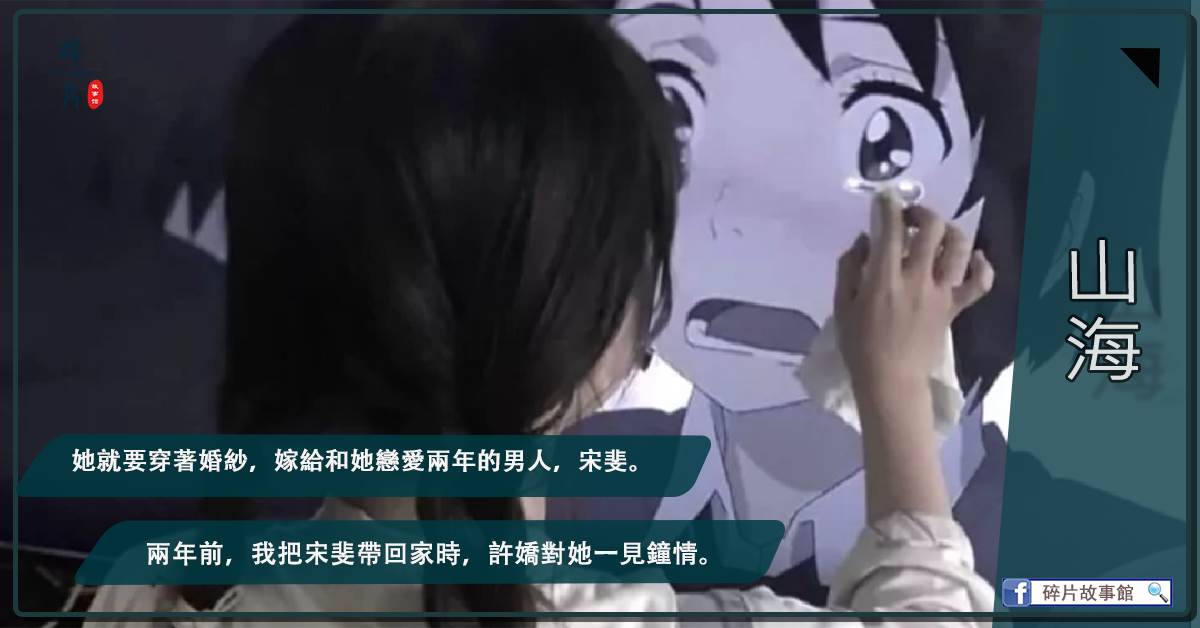《山海》第10章
她那仿佛打量陌生人的目光,讓許澤打了個寒顫。
「怎麼了……媽?」
我媽搖搖頭,啞聲說:「回家吧。」
許澤現在只有高中文憑,沒有好點的公司會要他。
我媽讓他跟著我爸去家里的廠子,準備以后接手家業。
因為確實辛苦,許澤不情不愿。
但也知道別無他法。
而就在他進廠后的第三個月。
發生了一件事。
一個工人的右手卷進機器里,被絞碎。
鮮血淋漓地送到醫院里,勉強保住了性命。
但他妻子剛生產不久,孩子還小,家庭從此失去了頂梁柱。
而我爸,鉆合同的空子,最后不但沒有賠償,反而以操作不當致使機器損毀為由。
向那個工人索要賠償。
天理昭昭,報應不爽。
工人出院后,帶著一把刀闖進廠子里,找到我爸,用架在脖子上的刀刃,逼著他把兩只手都塞進了機器里。
這一幕發生的時候,許澤就站在旁邊呆呆地看著。
那是他的親生父親。
可他甚至不敢上前奪下那把刀。
只敢在事情發生后,把我爸送進醫院,然后給我媽打去電話。
我跟在她身后飄進醫院。
看著我媽走過去,對著無措慌亂的許澤就是一巴掌。
「那是你爸爸!你就不能制止一下,救救他?!」
許澤被打得眼圈都紅了,囁嚅著說:「媽,那人帶著刀啊。」
多可笑。
他敢為一個女生和同學扭打成一團。
可是不敢為一直很疼他、還準備把家業給他繼承的父親奪刀。
我爸的右手沒能保住。
左手也只剩下兩根手指,光禿禿的手掌看起來猙獰恐怖。
他說疼。
我媽盯著紗布上的血跡,忽然怔怔地問。
「你說那天晚上,桃桃是不是比這還疼?」
「她一直叫我,一直叫我……我沒有聽見。」
「我怎麼就能,沒有聽見呢?」
沒有答案。
媽媽,你怎麼現在才懂。
有些問題,永生永世沒有答案。
15
我爸出院后,變得頹然沮喪。
而許澤的能力,一個人又撐不起這個廠子。
一籌莫展的時候,許嬌帶著宋斐回家了。
她提出他們夫妻和許澤一起管理。
我媽盯著她的臉看。
那張嬌美的臉上,有幾塊淡淡的青紫色。
似乎是受傷后,又快要痊愈的。
「怎麼回事?」
我媽把許嬌拉進房間里,問了兩遍,她就哭了。
「許桃死后,宋斐對我就一直不太好,再加上之前爸說要把廠子給許澤,他就和我大吵一架。說爸再疼我有什麼用,家業還不是給兒子。」
「我和他吵了一架,他說許桃根本就不是那麼壞,說如果不是我們在他面前造謠,我半夜潛進他房間勾引他,他肯定不會和許桃分手的。」
「他還動手打了我,說我故意不接電話,害死許桃。」
「媽媽,他怎麼可以這樣對我呀……」
許嬌一路嬌生慣養地長大。
他們連重活兒都舍不得她干。
何曾受過這樣的疼痛。
她嬌滴滴的,泫然欲泣地看著我媽。
淚盈于睫。
希望她能給自己做主。
可我媽只是面無表情地看著她:「他說的,有錯嗎?」
許嬌整個人僵住,不敢置信地看著她。
「你多恨許桃啊。許桃從來不主動聯系你,她給你打電話,肯定是有急事,甚至有危險。」
「你掛掉電話的時候,在想什麼,你心里清楚。」
她漠然地路過許嬌,走了出去。
我努力地倚著墻靠著,仿佛這樣就能給自己一點支撐的力量。
原來我媽也可以很聰明。
也可以很敏銳地洞察出許嬌的小心思。
也可以無情地戳穿她的小把戲。
挑破她對我的惡意。
可為什麼我活著的時候,一次都沒感受過。
一定要死后,才來告訴我這一點。
晚飯的時候,他們又吵起來了。
無非是為了那個廠子的歸屬。
我從未肖想過。
但許澤和許嬌都理所當然覺得那是他們各自的。
他們開始爭吵,互相揭短。
但說來說去,話題竟然都繞不開我。
許澤說:「當初你弄壞了媽的絲巾,還不是推給許桃,你怎麼有臉說我?」
許嬌說:「許桃高中的時候為什麼被霸凌,還不是你上學路上解了她的內衣帶子就跑,正好被她們年級那幾個混混看到?」
「許桃一去上大學,你馬上讓正在氣頭上的媽把她的臥室改成琴房,你有什麼天賦,學個屁的鋼琴,以為別人不知道你的心思!」
「你有臉說我!不是你攛掇媽媽,讓許桃報本地的大學,這樣她就能幫忙做家務,你連自己的內褲都不愿意洗,都要丟給許桃!」
吵吵嚷嚷。
鬧得真難看啊。
我媽的臉色越來越蒼白。
她忽然站起身:「夠了!」
「許桃都死了,你們還不肯放過她!」
這個一地雞毛,腐朽難看的家庭。
像一幅徐徐攤開的恐怖畫卷。
我媽撐著桌面,胸膛劇烈地起伏:「許桃死得那麼慘,連鄰居,連她的房東聽到,都會哭,可你們一滴眼淚都沒為她掉過。」
「現在來整這些爛事,還要把她扯出來——」
「你也夠了。」
我爸倏然打斷了她,「我體諒你喪女之痛,但你是不是做得太過分了,趙素?我在醫院疼得整夜整夜睡不著,不見你來安慰我,就知道提許桃。
早上不幫我買早飯,也要回去擦她的遺照。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