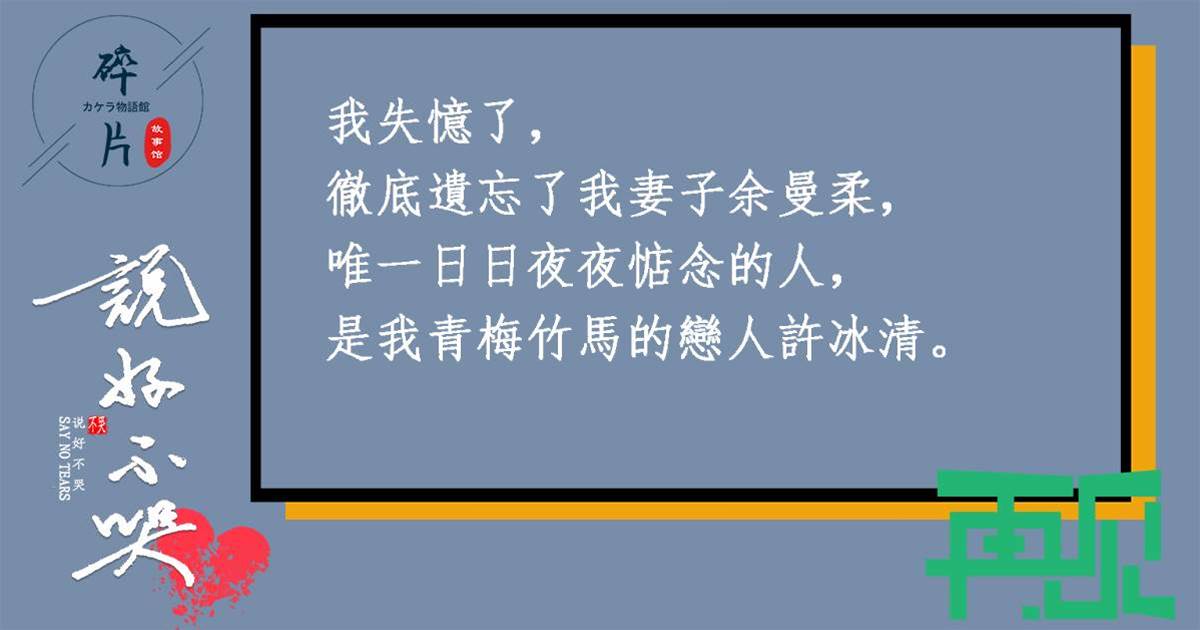《獨家記憶》第13章
我想不出原因,我只能說,此時潛意識里的那個曾經愛著余曼柔的周君遠占據了我的身體,他控制著我心臟,讓我那麼疼。
是什麼一種感覺呢?
就好像自己封存在角落里的一件東西,你覺得它并不重要,可是某一天突然被人告知它摔壞了,不止壞了,你甚至連看它一眼的機會也沒有了,因為它在老早以前,在你不知道的時候已經被人扔掉了。
這個時候你才發現,你對它并不像你想的那樣不在乎。
也是到那一天我才明白,為什麼在過去的一年里我老也打不通她的電話,為什麼發過去的信息一直沒有收到回復,為什麼唯一次接通電話還是她朋友接聽的。
我到現在依然記得她朋友當時的語氣,冷冰冰的,沒有一絲溫度,她說:“周君遠,請你以后不要再打電話過來。”
現在想來,她這冰冷的語氣里應該是帶著恨的,但那時我以為是因為我結婚,她不想再與我聯絡,才讓朋友替她接這一通電話把我打發了。
我想過她可能有了新的生活,想過她恨我入骨,卻從未想過她會因為我而自殺。
那天晚上,我給余曼柔的朋友撥電話,開始仍然是不肯接,幾通之后她終于接起來,語氣不善,問我:“干什麼?”
我不知道自己的聲音是什麼樣的,但總歸是不正常的,我說:“為什麼不告訴我?”
電話那邊一陣沉默,她自然是明白了我的意思,許久才說道:“她不讓,她留了遺囑,不讓告訴任何人,除了警察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
那麼許冰清從哪里知道的呢?自然是從那個多嘴的女人那里聽來的,至于她又是從哪里知道的,那就要問問她那個在警局里做事的親戚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在這個時候還有心情去想這些事情,大約是因為本能地想回避一些不愿意面對的事情,便尋了這樣一件不相干的事情來想。
我從她朋友那里得來了兩件她留下的東西,一件是木雕的男女娃娃,一件是她曾經用的手機。
她說:“這是你們兩人共同雕刻的,這個手機……里面有一些你們的視頻、照片。”
我把那個五六十公分的木雕帶到我和余曼柔曾經的家里,把它放在那些小動物的中間,至于手機,我沒有打開,我把它和那兩個娃娃一起留在了那里。
我還有家,我還有許冰清,我不能讓自己一直沉浸悲傷里,我告訴自己我只能傷心那一晚。
我一直是這樣告訴自己的,直到某一天,那個手機里突然出現一條生日提醒。
那天是我生日的前一夜,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就想回到曾經的住處去看看。
那個時候其實已經快要凌晨十二點,我在外應酬后請了代駕,設定好的路途行駛到一半,我問代駕是否可以更改路線,代駕說可以,于是他便帶著我來到了那個我生活了四年的地方。
就在我像之前那樣擦拭那些木雕的時候,放在工作臺抽屜的手機突然發出幾聲陣動。
在我生日這天的零點,她做了一條提醒,上面備注了文字:老公阿遠的生日,嗯,不能忘記呢。
很幼稚,很小孩子氣的一句話,但我看著這一句話卻久久沒動彈,那個提醒的振動響了好久終于停下來。
我不知道出于什麼心理,快速翻到下一年,如我所料,下一年的同一天依然做著備注,上面的話與這次又不同:我要永遠和我的阿遠在一起,嘿嘿。
我又翻了一年,那里同樣寫了一句話:阿遠,你又老了一歲呢,按計劃,我們這一年該要小寶寶啦。
我瘋了一樣開始往后翻,下一年,下下一年……我發現每一年在我生日的那一天都做了提醒,翻到最后我的手已經酸了,而那時顯示的日期,我們已經近百歲。
她在這里這樣寫:哈,這一年我97歲了,而阿遠99歲,不知道我們兩人是不是都還在,我好怕阿遠會先走……想來想去還是我先走吧。
我終于再也控制不住,眼淚如急雨般從我的眼框里落下來。
我想起余曼柔向我提出離婚的那個早晨。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