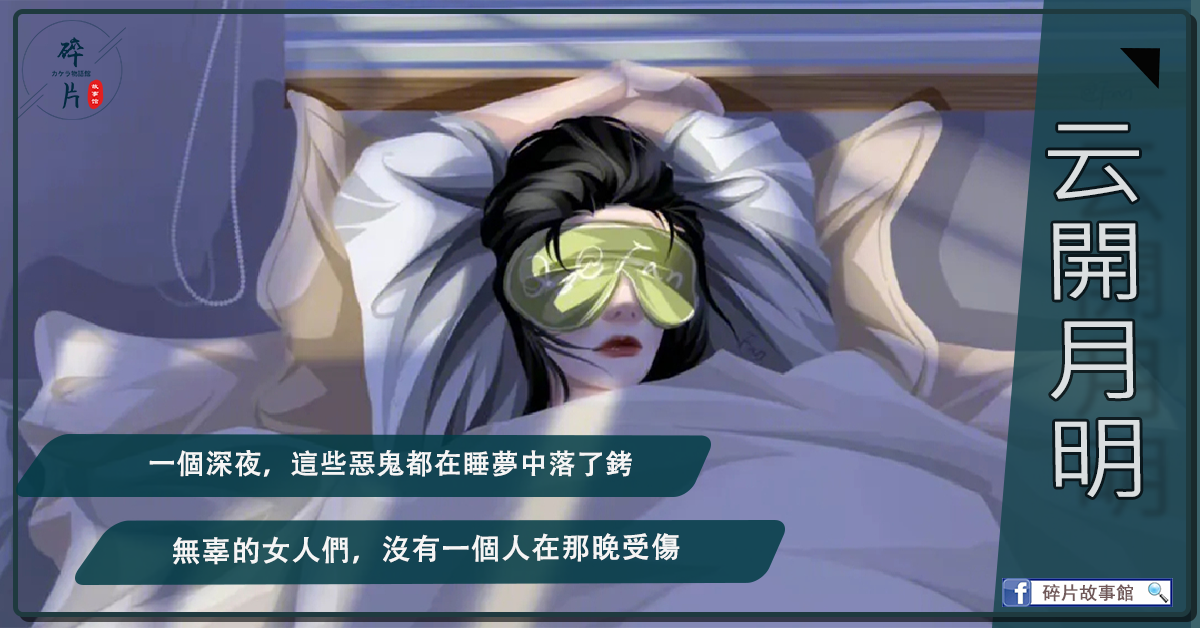《云開月明》第15章
下一瞬,我就聽見一聲清脆的斷裂聲,好像來自我身上。
那應該是腿骨斷裂的聲音,因為幾乎就在那個聲音之后,劇痛攝住了我的全部感官,我也總算失去了知覺。
14.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點。
我被羅大明拖回家之后又打了一頓,住回了牛棚和豬圈中間,沾了血的衣服依舊硬板一樣貼在身上,每天爬到食槽里跟豬牛搶吃的,夜里就縮在地上扒著草稈,眼淚都流不出一點。
幾乎和剛被拐來的時候一模一樣,唯一不一樣的地方是我自己。
我腿瘸了,也怕得要命。
我每天渾渾噩噩,提不起力氣想什麼逃走什麼求救,大多數時候都是安靜地縮在牛棚旁邊,打量著牛和豬的腿,再看看自己的。
也能走路,但骨頭歪了,走起路來應該會搖晃,和從前不一樣了。
不過,我還沒試過,自從那天晚上開始,我就沒再走動過一步。
被打斷腿的這段日子里,羅大明看我快死了,也沒怎麼折磨我,插門閂的那些人也不來了。不知道趴了多少天之后,他找了個村醫過來。
這些人也不想自己花錢買回來的玩意白白死掉,更不想馴養了這麼久,或許馬上就可以完全馴化的戰利品咽氣,所以每家每戶都會為挨打的女人請村醫。
不過不用猜,其他女人的情況也一定和我一樣,不是第一時間治療,而一定要等到再無完全康復的可能之后再治療——唱歌好的嚎啞了嗓子;寫字好的踩斷了手;會跳舞的,就讓她跛腳。
村醫走之后,我的腿就一點點好了起來,但我看著那條別扭的腿,經常會覺得那不是我的,很想用什麼東西砸下去。
我每天清醒地感覺到自己在一點點萎靡,卻每天又在痛苦自己為什麼不干脆瘋掉。
因為我想不明白,那些簡單的問題霧一樣勒纏住我,我卻怎麼也想不出答案。
我想不明白,我只是一個普通人,從小到大我一直善良熱心,從來沒做過什麼壞事,為什麼這樣的事要我來遭受?
為什麼偏偏是我,為什麼我非要在那天早上去菜市場,為什麼我要出門?
是我做錯了什麼嗎?
其實我心里也很清楚,這一切肯定都是肖維設計的——包括此時此刻,他也還在設計著我們所有人。
從一開始,拐賣的時候用同伙演戲就是圈套。他們事先安排自己人,一面假意幫我報警,一面讓心存善意的圍觀群眾「眼睜睜」看到我「欺騙」大家善意的全過程,讓大家對這種現象深惡痛絕,也讓我經歷希望突然破滅的折磨。
我甚至覺得,菜市場那群大爺大媽口中抱怨的:「前幾天因為有人呼救報警,結果最后發現是夫妻鬧別扭」「之前見義勇為跑來救人,卻發現求救的是拍短視頻段子的」,這好幾次「欺騙」都是他們之前故意設計的,為的就是讓好心人心冷,讓所有人形成刻板印象——他們以后遇到這樣的事,會下意識地認為對方是利用善意的騙子。
然后在擄走我后的車程中,他們一步一步踩著我心里的救命稻草摧毀,車牌是假的、人販子容貌是假的、報警電話是假的、每一個幫我的人都是他們同伙……
等到這一切把我們的希望全部砸碎,他們就開始驗收成果,把車開到加油站來考驗我們。
加油站這個考驗無非兩個結局,第一種是像我當時身邊的煞白女人那樣試圖逃跑,他們會故意放走去廁所里伺機想逃的獵物,眼看著她們跑出去求救,再由被求救的人親口告訴她們,她們根本逃不掉。
第二種就是像我一樣乖乖去廁所又回來的,這種省心的獵物在他們眼里應該可以稍稍放松一些,獵物本人免了皮肉痛苦,但一樣會從同伴的遭遇里明白外面的一切。
如果獵物里有聰明的,就再設置木亭子的考驗,或者其他考驗。每一步都是肖維事先想好的,每個局都是重復的,都是先給獵物生的希望,再狠狠把它踩碎,一遍又一遍地打擊折磨。
他們甚至周密地斷掉了每個獵物最后的念想——每個人的手機上,都有自己賬號發給親友師長、同事領導的、語氣和聊天習慣都和自己高度一致的消息。我恍惚記得肖維說,反正他也沒事干,發消息這個行為他會持續很久。
等我們終于到了這里,也不會有任何僥幸事件發生,每天依然是身體和精神的折磨。毆打、辱罵、凌虐、摧毀,每個人每天不知道會經受多少。
其實一路上的打擊,已經足以讓每個人變得疑神疑鬼,覺得身邊什麼都不可信。但即便是這樣,一旦遇到機會,每個人就還是會想要抓住救命稻草。因為沒有人愿意認命,承認自己真的、真的再也逃不出去了。
所以有那麼多倔強的生命,那麼多不甘的女人,淌著血也要反抗——或許也有人猜到真相,可她們沒辦法了,寧愿相信騙子是救贖,也不愿再做驚弓之鳥,日復一日地忍受無處不在的考驗和酷刑。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