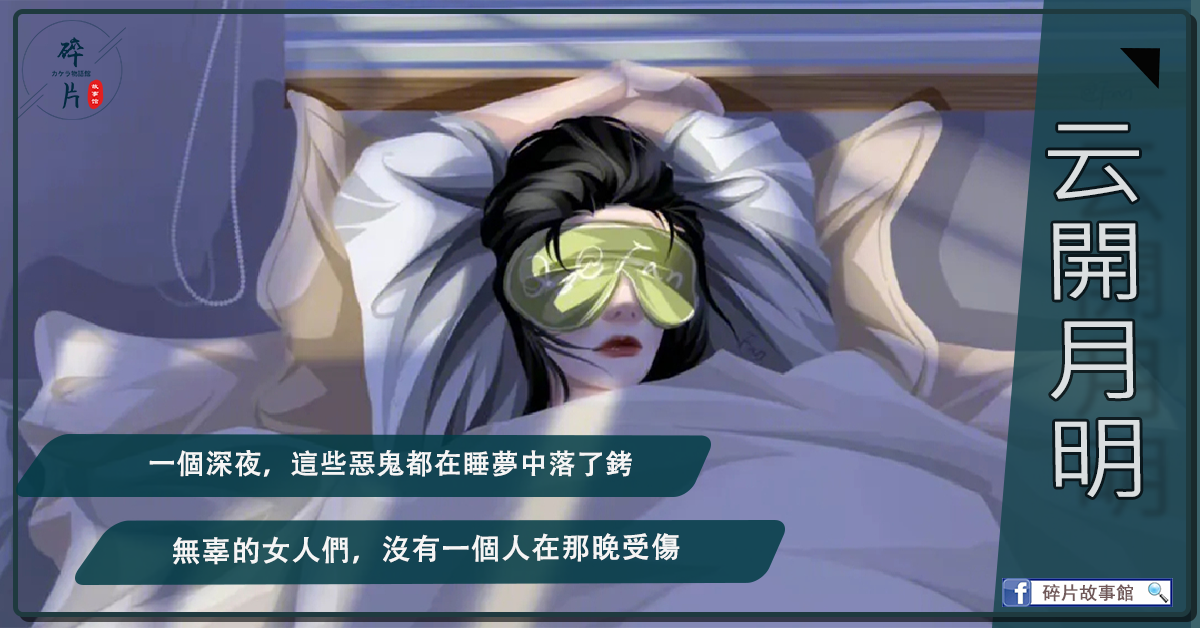《云開月明》第13章
他可能不只是外鄉人。
這些天我活動范圍擴大,曾遠遠地看到過他幾次,都是在很隱蔽的地方,不過每一次見的都是不一樣的女人。
那些女人都有個共性,她們每天一副心灰意冷的樣子,我卻能在她們眼睛里捕捉到一點細微的、盡力藏住的光亮。
我不認為是「外鄉男人」廣撒網騙感情,也不覺得一點施舍或者虛無的承諾能讓那些試過無數辦法的渾濁眼眸發亮。幾次看到男人距離都太遠,我看不清他長相,卻記得很清楚,他很挺拔,像一柄劍。
他會不會是……
「羅大明家的,動作快點,徐松家的解手去了,你替一替她。」
我胡亂點頭,卻被突如其來的腹痛墜得冒冷汗,急忙扯住下命令那女人的衣角。
女人啐我一口抱怨麻煩,但踢了幾腳后見我也真的干不了活,還是一臉嫌惡地帶我去一邊解手。
我疼得快要昏死過去,監視我的女人連連向前走,嫌惡地捂著鼻子,背對著我。
腹痛稍稍緩解,我終于松了口氣。
也就在這個時候,我后背的衣角被什麼扯了扯。
我整個人一激靈,卻理智地沒叫出聲。回頭看向來時空空的草垛,那里竟然有個男人!
這人長相我從未見過,但氣質一看就是這幾天我注意到的那個男人。
他終于來找我了!
男人沖我比著噤聲的手勢,一手遞過來一個手機。
手機屏上左、右兩張圖片,他滑了一下,第一張是照片,第二張圖片里是文字,他用這種方式和我交談。
和我猜的一樣,這個男人是潛進來做臥底的,第一張圖就是他的證件照片。
第二張的文字告訴我別怕,他們的行動馬上收網,他能救我們所有人出去!
我手輕顫一下,唇卻抿得死緊,只低頭盯著手機屏幕。
因為那張圖片上也說了,他需要我幫他個忙,這件事很重要,如果辦不成會影響他們收網的速度,我們可能會需要再忍耐一段時間。
圖片上說,如果可以就點頭,不可以就搖頭,他一樣會救我出去。
我沒搖頭,也沒點頭。
我能被從干活的場地帶到這邊,是為了解決內急。前面監視我的女人雖然還沒開口催促,但很明顯,能允許我們交流的時間馬上就到頭。
心跳一聲一聲,錘子一樣砸在我的耳畔,男人面色也逐漸焦灼,他應該是很需要我幫忙。
但我沒有任何動作。
包括男人又拿回手機,調出另外一張照片,上面說不管我愿不愿意幫忙,他們一定會救我出去。但我千萬不能對任何人說起這件事——他拜托的眼神投過來那個時候,我都始終沒有反應,沒答應他也沒拒絕他。
因為我太怕了。
如果是剛來這里的我遇見這個男人,我一定會迫不及待地幫他,我恨不能這個罪惡的村子頃刻消失,所以我一定會愿意加速他們一鍋端這里的進程。
可現在不一樣了,長期繼續的生活已經讓我變得瞻前顧后,我現在每天的期盼只是少挨些打,那些恨意和不甘不知道什麼時候起就開始模糊,連感官都逐漸遲鈍。
所以在他找到我的時候,我突然就遲疑怯懦,哪怕這場他見縫插針接觸我的「偶遇」
,實際是我自己思忖多日制造出來的。
更何況,我如果幫了他,他會不會幫我?他單槍匹馬來到這里,怎麼就能確保救所有人出去?
我如果按照他說的做,會不會只是一場好夢,他救了別人走,又把我留下?
再或者,會不會他們想做的根本做不到,暴露了他逃跑無妨,我卻得留在這里被打被折磨?
但我同樣不敢直接拒絕他。萬一拒絕了,惹火了他,他到時候故意跟村里人舉報我有二心怎麼辦?得罪了他,我肯定也完了。
所以那一瞬間我想到最好的解決方式就是逃避。不答應也不拒絕,我就一直沉默著。
我混混沌沌地回到羅大明家,隔著扎眼睛的頭發窺著月亮,漫天刺眼的白光烙得我眼熱,我蜷在豬圈旁邊緊捏著胳膊,忽然就顫抖起來。
我肯定做了個正確的選擇。
一定是正確的。
就算因為我犯慫,別的女人能獲救,我卻要繼續留在這里永遠不能被救,也沒什麼大不了,對不對?
因為還有失敗的可能啊,萬一逃不出去怎麼辦,萬一失敗了被發現了怎麼辦,萬一他們又要打我折磨我怎麼辦!
我賭不起了。
只要有百萬分之一失敗的可能,我就永遠都不敢賭。
反復和自己確認了這個決定的正確性,我竟然荒謬地覺察到一點甘甜的滋味。
起碼我每天可以活動,可以上桌吃飯。而不是被發現后割了舌頭扔進黑屋子里,不是被綁在柱子上每天被村里的人毆打泄憤,也不是被剁碎灑在老賀家后頭那塊宰命的荒地里。
門外腳步聲乍起,我連滾帶爬地蹭起來,躲著眼伺候羅大明。
一連幾天過去,羅大明對我似乎越來越滿意,看他反應,應該是沒人嚼我舌根,我稍微放心,每天卻還是渾身發毛。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