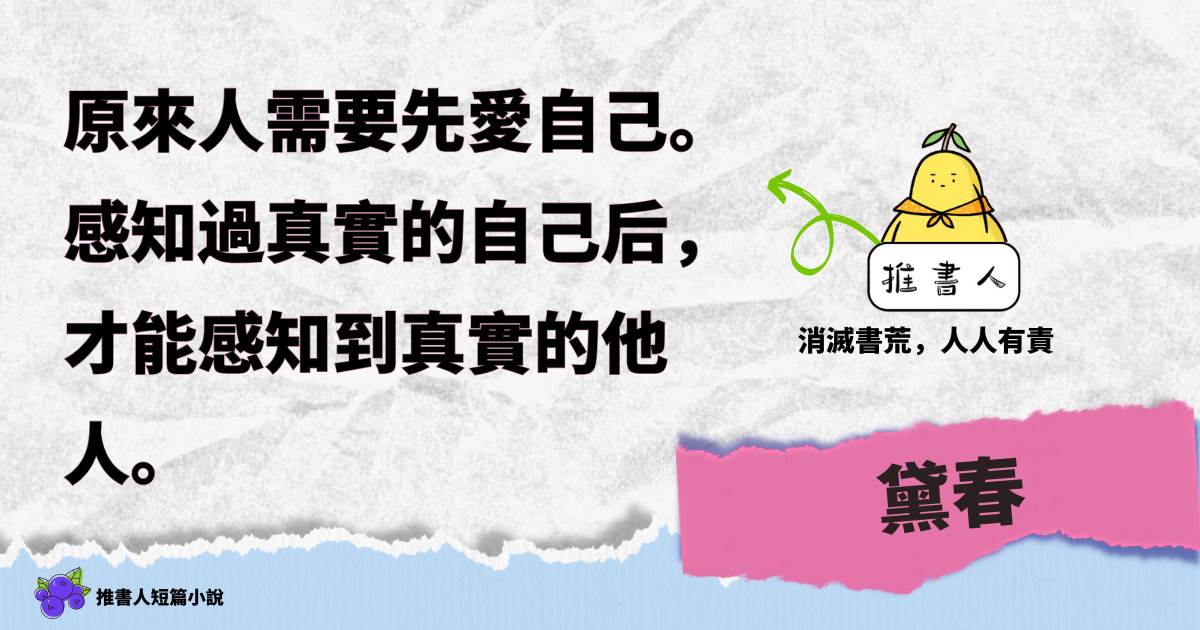《黛春》第13章
蘊含復雜情緒的眼眸一瞬堅定,他回答:
「不離婚,就按你的打算繼續生活。」
我知道,作出決定的過程對他而言有多麼痛苦。
我有那麼長的時間變得堅決,他卻要在幾天之內作出取舍。
可惜,別無他法。
我爸因為堵車在路上耽擱了好一會兒。
他匆匆趕來,看到我和裴衡就站在墓碑前溫和交流,心情好了不少。
祭奠完,他非要讓我們兩個回家吃飯。
然而,路上我接到了時露的電話,飯還是沒吃成。
時露因為高燒暈倒在路邊,被路人送來了醫院。
我趕到急診室的時候,她在輸液,才恢復清醒沒多久。
「要不要喝點水?」我看到時露嘴唇起了干皮,關切地問。
她輕輕搖頭,臉色因為發燒不正常地發紅。
我環望四周,問,「你沒告訴余澈嗎?」
她有些艱難地開口,「他正在跟客戶開會。」
見她神情有點失落,我安慰她,「沒事,我在這里陪著你。」
看她依舊虛弱的樣子,我讓她繼續睡覺。
直到輸完液,時露還在睡著,而余澈依舊沒有過來。
我把床頭的杯子灌好了水,方便時露醒來可以直接喝。
然后我下樓去附近的一家粥店買了午飯回來。
回來的時候,在樓底下碰到了裴衡。
「你怎麼過來了?」裴衡的頭發被風吹得有些凌亂,眉眼間的沮喪清晰可見。
我想短時間內,他都沒辦法恢復了。
他接過我手中的袋子,跟著我一起回到急診室。
「我怕你一個人照顧不過來。」
我不解,「你怎麼知道只有我一個人?」
裴衡挑挑眉,解釋說,「我碰見余澈了。」
「他在哪?怎麼還不過來?」
說到這個,我覺得余澈不夠重視時露。
「中午和觀致一起在外面吃飯的時候碰見的,他好像在和同事吃慶功飯。」
我有些無語,這麼離譜的嗎?
「你別和露露說這件事。」馬上要到了,我叮囑道。
她現在生著病,本來就脆弱,要是知道了肯定更難過了。
我都不知道余澈這樣的態度,她還要和他共度余生,這到底是何等的情深。
陪著時露吃了飯,和她又聊了些本科的趣事,我又跟著她吐槽了一下工作,她看上去精神和氣色都好了些。
這期間裴衡就坐在床邊空閑的凳子上處理工作,時不時出去接打電話。
在裴衡不知多少次起身出去的時候,時露不好意思地說,「思思,我看你們挺忙的,你是不是還特地請假過來的。我這邊沒什麼事了,你們先回去吧。」
我趁機捏了捏她的臉,溫度似乎已經降下去了。
「別擔心,今天本來因為我媽的祭日我就請了假,正好在醫院陪你。
「至于裴衡,是他自己非要跟過來的,你不用管他。」
時露打趣地笑起來,「裴衡對你真上心啊。」
我面上笑著,心中唏噓。
時機很重要,錯過了用心就不再有意義了,只剩下了無力。
慢慢地,裴衡就會習慣,不再對我用心了。
而我們就會互不相干地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做著最熟悉的陌生人。
「叔叔最近怎麼樣?」
「他現在也不當班主任了,只要給兩個班上上課就可以了。畢竟再過兩年就退休了。」
「叔叔以后的日子都打算一個人過嗎?」時露試探著問。
我不由嘆氣,「我也不知道。
我當然希望他可以再找個合適的人做伴。但我媽去世得太早又太突然,給我爸留下了太多遺憾。」
「可這也過去很多年了吧。時間會沖淡一些吧。」
「時間對有些感情并不是那麼管用。」我心生感慨,「我媽是我大二那年出的車禍,這都十年了,我爸依舊是除了上課只剩下懷念我媽了。」
時露拉住我的手,輕輕拍了拍,表示安慰。
忽而,一個高大的身影籠罩住了部分陽光。
我轉頭,是余澈。
奇怪的是,時露看到余澈沒有一絲開心,嘴唇甚至顫抖了起來,拉著我的手還出了薄薄的冷汗。
余澈那雙深邃無波的眼睛正以堪稱犀利的目光審視著時露,而時露卻避開了。
我搞不清發生了什麼。
此時,接完電話的裴衡回來了。
他似乎發覺了凝滯的氛圍,特意輕快地招呼我。
「小意,既然余澈來了,我們就先走吧,別打擾他們兩個了。」
我看向時露,用眼神示意,問她需不需要我留下來。
時露回我,「是啊,思思你和裴衡先回去休息吧。」
盡管不放心,我還是離開了。
13
我搬回家里住了。
我和裴衡正常地上下班,除了必要的對話外幾乎沒什麼交流。
這對裴衡來說似乎并不好受。
他之前在家的輕松和專注全然不見了。
取而代之的是發呆和凝望。
我總覺得他說話做事更小心了,像是害怕越界讓我生氣。
盡管他比從前疲憊憔悴了,可我并沒有因此心軟。
我何必對他關心,讓他產生可以重修于好的錯覺呢?
這樣看得到卻親近不了就已經足夠痛苦了。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半個月。
裴衡的生日到了。
裴衡姑姑對他的疼愛一向不遜于自己的孩子。
按照慣例,會特地為他辦場生日宴會。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