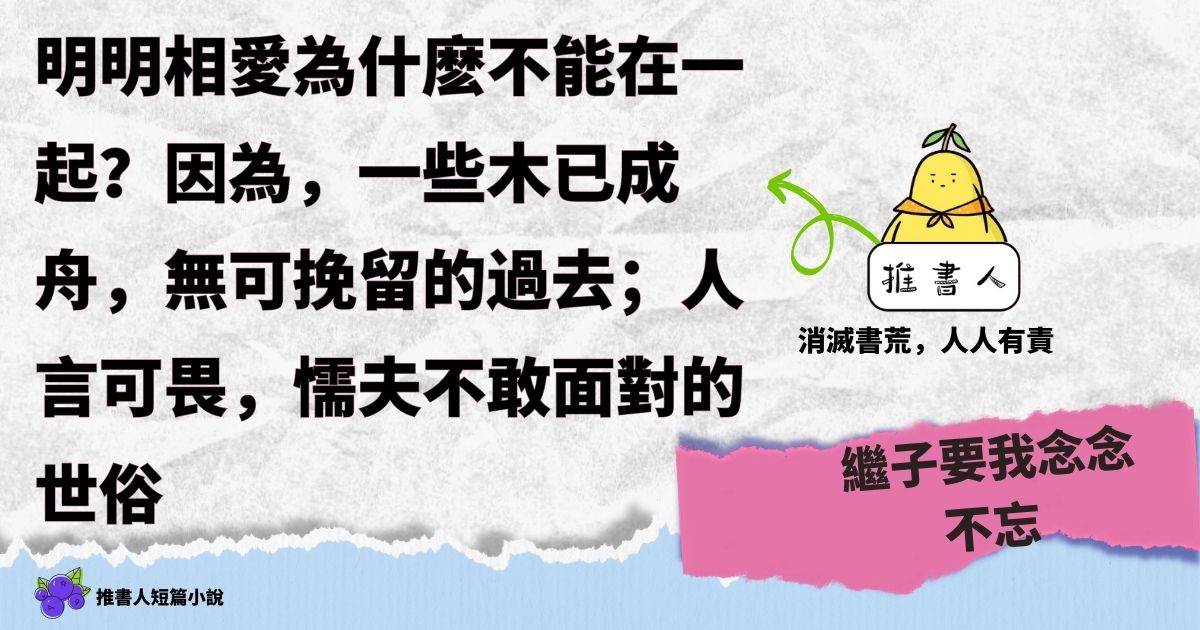《繼子要我念念不忘》第11章
這張照片,還是在徐堯的墓地前,背景里有朦朧細碎的小雨。
手指一張張劃過——
一開始,少年筆直站在前方,只留給我一個背影。
下一張,我捕捉到他回頭偷看我,光影交錯,明暗之間,少年五官出落得引人多貪心。
再下一段,是一個短短的視頻。
濕潤的土地和雨天,那種潮蒙蒙的濕氣撲面而來。
鏡頭開始晃晃悠悠著,似乎是我不小心觸碰到了錄視頻的鍵,隨后又大意地將手機丟回了口袋里。
我聽見視頻中,我上前,隨口一句關心,問他,「要不要撐傘?」
然后我自顧自地把傘分他一半,大概比一半還要多——因為鏡頭泡的水看起來更多了,甚至雨聲打下來的聲音都變得悶了,更多的雨水澆到我的半邊肩膀,半邊口袋里。
他怔了好一會兒,「你怎麼在這兒?」
我回答得一本正經,「我是你的繼母。」
他緩緩深吸口氣,想說些什麼,又低下了音量。
只有徐驍自己知道,那天被風和雨吹走的那幾句話。
他后悔來了父親的葬禮。他小時候一直以為自己是個孤兒,父親根本沒有盡過責任。大概兩人只碰過他生父死這兩面。他對親情一向沒什麼執念。
那麼后悔的是什麼呢?
風和雨聽到了,窺見到少年隱秘而猛烈的心意。
徐驍輕而更輕地說,「早知道這樣,我就不來了。至少那樣……我還能堂堂正正、毫無顧忌地說愛你……追求你。」
記憶中的當事人沒能聽清。
只當是這個剛成年的,不成熟的繼子,傷心過度,胡言亂語。
如今我卻在他走后看到了。
與此同時,伴隨著,我虛構的記憶一寸寸崩塌——
沒有任何預兆地,我恢復了所有有關徐驍的記憶。
徐驍成功的做到了,令我念念難忘。
我起身離開相親現場,身后的弟弟問我去哪。
我說,「去祭奠前夫。」
今年是徐堯走后第五年,算起來我有 31 歲了。
離開情侶餐廳后,我沒有去看徐堯,反而去了徐驍的墓碑前。
今天又是場毛毛細雨,我仰臉看了眼黑色的傘邊。
雨滴打轉,空氣泛冷,想了想,我松手丟掉它,留在了徐驍的墓前。
后來安安穩穩的生活中,縫隙時間,也會想起徐驍。
就連戀愛都難免受了影響,不只想起一位姓徐人士了,這下是兩位。
想起徐驍的時間更多,太多,多到令人難過。
就連夢里都三番五次地見到他——
我有挺多話想和他說。
但那些話臨到嘴邊,見著夢里笑著的他,我又吞吞吐吐,顯得語無倫次。
夢醒后,我悵然若失,又無可奈何。
他最后說,算了,還是讓我忘掉他吧。
但我也有太多無能為力的事情,于他,于自己。
我無數次拒絕他,堅定自己,其實也曾被他的癡心融化,為他有過難言之隱——
這一生太多事,唯有一件令我輾轉反側、念念難忘。或許是那年葬禮,不該為他撐了半邊傘;又或許是,沒能同他一直撐傘走下去。
18
「番外:下雨天記得帶傘」
假如同徐堯墜入愛河、火速閃婚之前,他受不住內心的譴責,主動朝我交代了初戀和懷孕的事情——
「我曾經年少不懂事,和她睡覺時沒注意過措施,不小心懷過一個孩子……」
徐堯端倪著我的臉色,紅著眼握住我的手,滿是愧疚,「念念……你放心,她說早就把孩子打掉了。
」
我滿臉問號,趕緊用力甩開了徐堯的手。
嫌臟。
他話里話外求我原諒,卻對過去嗤之以鼻,一副撇清責任的態度。
明明年少不懂事懷了孩子,再打胎的初戀才更趨向受害者。
他卻只忙著回顧自己的后悔。
我不怎麼喜歡不負責任的人。
尤其是以后要托付終生的存在,再怎麼魅力多金,人格有明顯缺陷的存在下,都等同于虛無。
其實最主要的,還是令我厭惡。
我甩了他一巴掌,跑到附近的快餐店里,用洗手液搓了個干凈。
隨便買了點兒什麼快餐,我邊咬幾口,邊懶散步行。
走到一個巷口時,有只模樣漂亮的橘貓朝著我喵喵叫。
它毫不設防地搖尾翻肚皮,小眼卻一直盯著我手里的吃食。
我隨便揪了口面包蹲下來喂它,心想今天的好運氣都攢在這兒了。
身后卻有個年輕的少年開口喊,「前面那個,這貓是我喂的。」
他沖上來,一把蹲下抱走橘貓,再抬眼看見我時,他喉結一哽,愣住了。
沉默了那麼幾秒,我起身要走人,他卻忽然乖聲喊住我,「姐姐。」
「啊?」
他噎了噎,掩飾著拘謹和嘴硬,改口了剛剛的那番說辭。
「貓叫咪咪……」他沒敢看我,黑睫微垂著,瞥向懷里的貓兒。「我叫徐驍。」
「和我前男友一個姓啊。」
他眉梢微皺,「我也不怎麼喜歡這姓,不過院長說這是我媽起的。」
「行吧,我叫步念念。咪咪咪~」我逗橘貓。
少年一見鐘情,悄悄地藏住春心暗懷,不動聲色地偷瞧我。
我也裝作不知道。
沒辦法,我還挺吃他這款。
我們莫名其妙地就這樣維系著關系。
直到一月左右后,下雨天,我再去小巷找他,咪咪卻不知道偷跑到哪兒去了。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