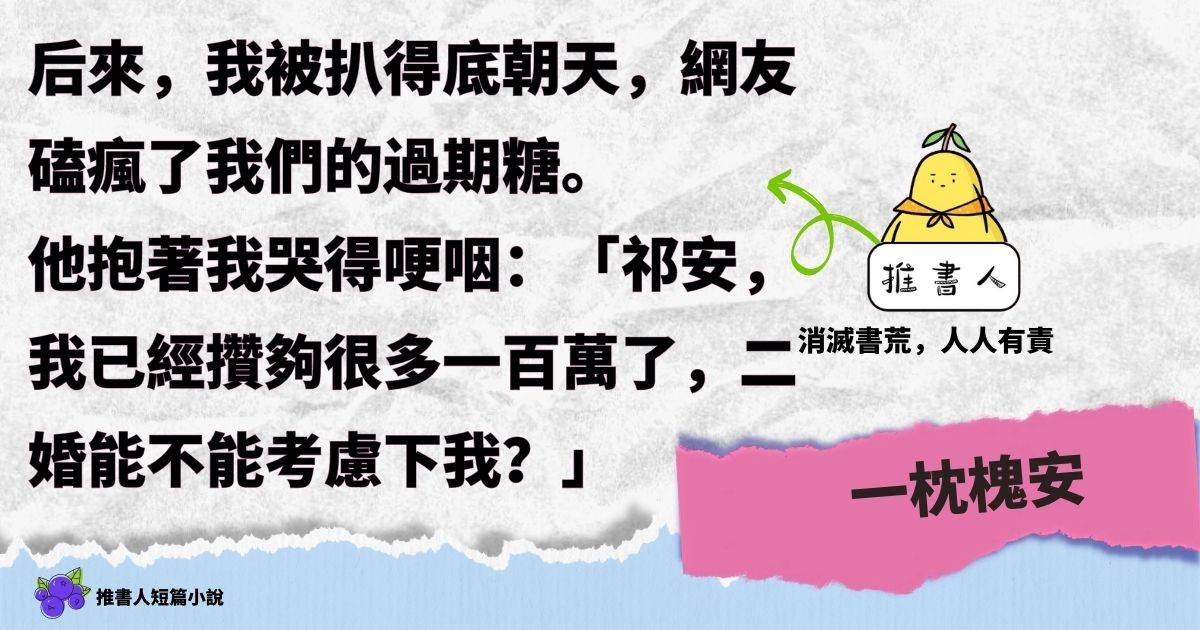《一枕槐安》第1章
電影《槐安》首映時,導演陳槐序說這部電影他籌備了十二年,是給一個人遲到的承諾。
記者問:「是很重要的人吧?」
他自嘲:「一個終生難忘的騙子。」
后來,我被扒得底朝天,網友磕瘋了我們的過期糖。
他抱著我哭得哽咽:「祁安,我已經攢夠很多一百萬了,二婚能不能考慮下我?」
1
520 這天,導演陳槐序的電影《槐安》上映了。
一時「槐安」二字,占據各個平臺熱搜,半個娛樂圈都在轉發預熱。
首映設在了晚上十點,依舊座無虛席。
從籍籍無名到天才導演,他只用了五年。
伴著滿場的尖叫聲與歡呼聲,陳槐序現身首映禮。
擁有著絕佳的皮相與身材,站在幾位演員身側,依舊毫不遜色。
坐在影廳最后排的角落,我望著臺上的男人,一時失神。
有媒體提問:「聽說《槐安》這部電影陳導籌備了很久,能和大家分享一下背后的故事嗎?」
他微微頷首,目光微微掃過全場。熟悉的聲音回蕩在影廳:
「這部電影我籌備了十二年,是給一個人遲到的承諾。」
十八歲時,他揮著電影學院的通知書對我說:「祁安同學,以后我要將我們的故事拍成電影。」
一別經年,黃粱一夢。
幾百人的間隔,是分手后,我們最近的距離。
聚光燈打在他臉上,勾勒出深邃的眉眼與英朗的五官,那麼近,又那麼遠,虛虛實實,不甚真切。
明明知道他視線觸及不到自己,但看到那張臉時,又忍不住亂了心跳,手指不由得絞緊,掌心的汗沁至攥得發皺的電影票根。
記者問:「是您生命中很重要的人吧?」
他微微一笑,嘴角勾起一抹似有若無的笑,自嘲道:「是啊,一個終生難忘的——騙子。」
五年前很尋常的一天,我望著廚房里他的背影說:「陳槐序,我出去一趟,你以后少抽煙,照顧好自己啊。」
他聽話地點了點頭,還在忙著做我愛吃的咖喱雞。
那天我沒有吃上他的咖喱雞,因為我抱著我們養的貓出門后,再也沒回來。
后來某次采訪,提及食物,他說最討厭咖喱雞。
人群中某記者又提了句:「那陳導對《槐安》的票房目標是多少呢?」
他眼神微動,勾了勾嘴角,聲音蕩在影廳:
「一百萬吧。」
主持人打趣他的謙遜幽默。如今「導演陳槐序」五個字代表著票房保障,金額都是以億來計算的,一百萬自然是個玩笑而已。
臺上臺下頓時笑聲一片,唯有我忍不住眼眶發熱,心里陣陣酸澀。
因為二十二歲那年,他抱著我說:「祁安,等我攢夠一百萬我們就結婚好不好?」
后來他攢夠了好多個一百萬,但早已沒有了「我們」。
人群中不知誰好奇問了句:「陳導為什麼要把首映設在晚上十點呢?」
他淡然一笑:「看完電影后,你也許會發現答案。」
2
燈光熄滅,電影開場。
「導演:陳槐序」五個字散去后,畫面切至學校禮堂,藍白校服的男生氣喘吁吁地喊著:
「陳安同學,能不能把你的高考志愿給我抄一下!」
一陣陣起哄聲響起,校長不耐煩地瞪他一眼:
「祁槐你有病吧?三百分和六百分能填一個志愿?」
影廳響起一片笑,只有我再也壓抑不住眼里的淚。
眾人在看故事,只有自己在照鏡子。
——
十八歲懵懵懂懂的年紀,喜歡一個人的悸動,就像吹在心尖的陣陣帶著槐香的夏風。
就像他的名字——槐序。
我偷偷翻著資料探究著關于他的一切:槐序,古時指六月,又指夏季。
世間溫柔,不過是芳春柳搖染花香,槐序蟬鳴入深巷。
我想如果青春有聲音,那一定是教室的讀書聲和窗外的蟬鳴聲。
暗暗計算著,每月一次的座位平移,還有多久我們會成為同桌。
十七八歲的年紀,暗戀一個耀眼的人,潛意識中總會無比自卑。
我羨慕陳槐序,他像個小太陽一樣,是富足家庭滋養出的骨子里散發出來的自信。
彼時,我上有姐姐下有弟弟,是最不受寵的,身上套著姐姐穿剩的衣服,自卑得不敢抬頭。
他不愛學習,總是抄我的作業,將根號 2 抄成 52,將「奧斯曼帝國」抄成「奧特曼帝國」,叫人哭笑不得。
他喜歡拿著相機拍 vlog,記錄著身邊的一切,又經常說些莫名其妙的話,逗得我滿臉通紅后,又惡劣地按下閃光燈,我又氣又急不想理他。
可他座位在里面,每次晃晃蕩蕩地拖到上課前一秒回來,又故意在我耳旁提高音量說一句:
「我回來了~」
我不吭聲,默默前移,他卻故意在卡在我身后,略帶為難:
「祁安同學,我進不去。」
后桌的同學好奇問他,為何每次都說一句「我回來了」。
他挑了挑眉,支著下巴側頭看著我,小聲嘀咕著:
「我提前練習一下。」
夏日蟬鳴陣陣,頭頂風扇呼呼吹著,歷史課,我聽得認真,他睡得香甜。
老師正義憤填膺地講著八國聯軍侵華,情緒激動之時,一拍桌子。
陳槐序猛地驚醒,臉上壓出了紅痕,嘴角還掛著口水,迷迷瞪瞪望著我喊了句:
「祁安同學……」
我望著他那副尊容,忍不住笑了。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